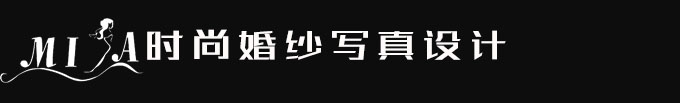- 邮箱:
- admin@eyoucms.com
- 电话:
- 0898-08980898
- 传真:
- 0000-0000-0000
- 手机:
- 13800000000
- 地址:
- 海南省海口市
1995年1月,中国首届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在云南西双版纳召开。当时我以华东师范大学旅游系副教授、在职博士研究生身份与会。会上遇到了时任北大城环系自然地理教研室主任的卢培元教授,我向他表达了想到北大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意思。卢教授当时正在创办北大旅游开发与管理专业,并且把课程设置带到西双版纳会上与大家交流。他对我的想法十分支持,回北京后很快与陈传康先生沟通,促成了我到北大地理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计划的实现。
1997年1月我进站后不久,就在陈传康先生和王恩涌先生的支持下,创建北京大学旅游规划研究中心,后因不断扩大研究领域,将其更名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卢教授也一直对我的状况表示关心,多次鼓励我在北大的学术发展。我进站时卢教授创办的旅游开发与管理本科专业虽然后来种种原因而停办,但是他和陈传康教授创办的这个旅游专业方向,不管是自然地理学专业,还是人文地理学专业,一直是北大地理学领域最受研究生报考者追捧的方向之一,当年不少本科年级第一、第二名学生免试直升研究生都会首选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研究方向。卢教授退休后患有眼疾,可是我一直认为他是北大城环系最具有战略眼光的学者之一。不幸的是,尊敬的卢培元教授也在今年的1月9日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不幸去世,享年91岁。北大旅游研究与人才培养,卢培元老师、王恩涌先生和陈传康先生一样,都是第一代开创者,值得我们尊敬与感激。
1997年陈传康先生不幸去世后,自然地理专业的旅游开发与管理方向面临暂时困难。这时候,虽已退休但一直受聘继续担任教学工作的王恩涌教授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承担了善后和继续推进工作。作为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以及另外三名博士研究生(崔凤军、刘家明、杨新军)的联合指导教师,王先生可以说是在陈传康先生去世之后北大旅研的中流砥柱。2007年,北大旅研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组织出版了一本《旅游发展与公共管理》的论文集(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在那本书的前言里就强调北大旅研在创始人的推动下聚焦于旅游公共管理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在该书后记(北大旅研的故事)中,分析了北大这一类综合性大学对于旅游研究来说不一定会有成建制的学科设置,但会容许旅游研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这种存在得益于王恩涌先生等几位知名教授的支持与帮助。有了他们的重大支持,才使得北大旅游教育得以连续发展。北大旅游研究与高等教育的今天,如果说有所成就的话,王恩涌教授的贡献诚不可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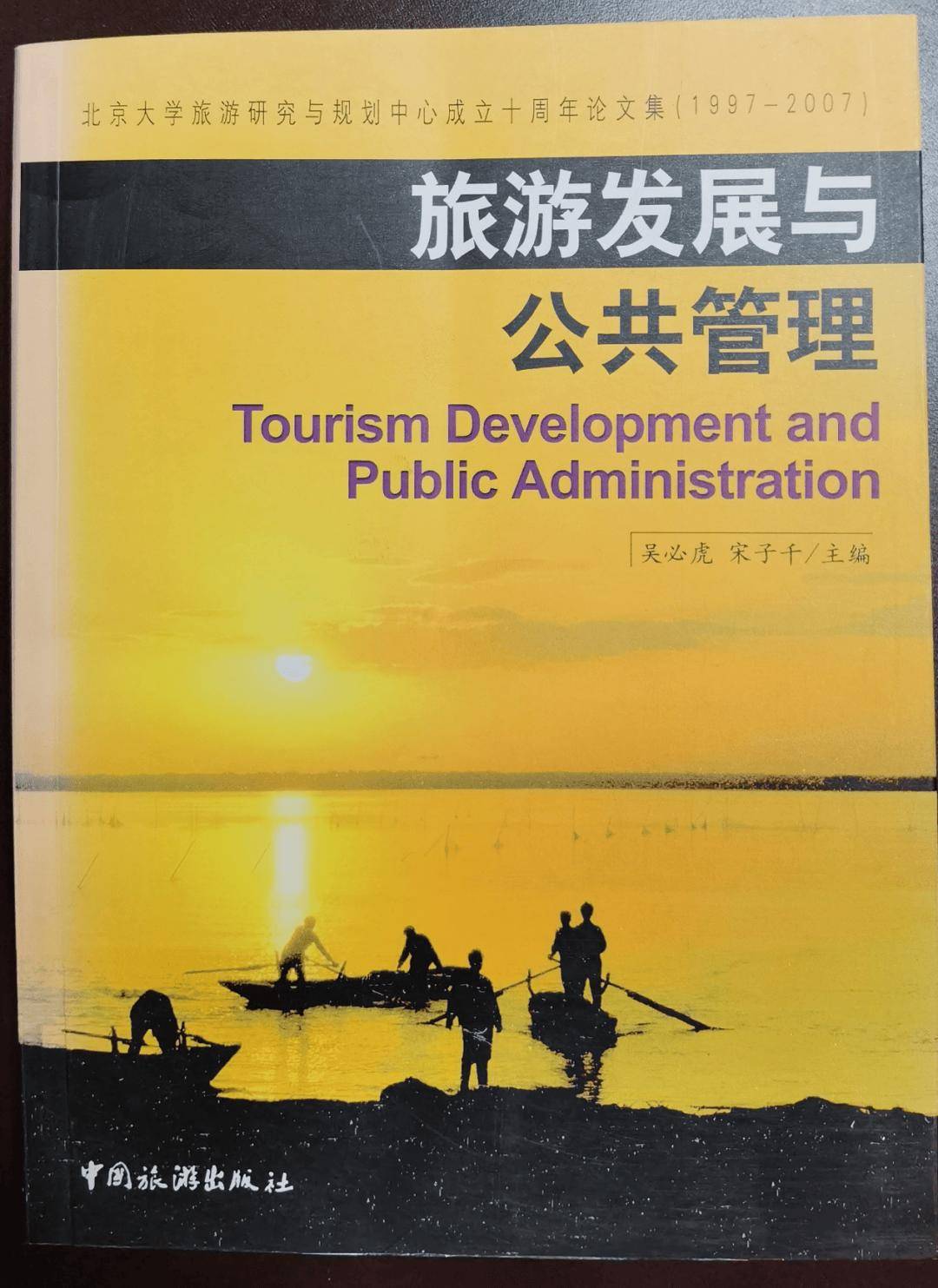
陈先生去世后系里安排我接任陈先生的旅游规划教学任务,办公室也搬到了原来陈传康先生的工位,与王恩涌先生有了十多年的对面而坐的亦师亦友的深交。我们不仅在逸夫二楼三层3363房间靠近电梯的那间办公室“促膝”而坐,而且一起参与了北京海淀区山后区域旅游规划、北京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黑龙江伊春市旅游规划、湖北大别山生态旅游规划、长江三峡旅游发展规划、吉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等一系列旅游规划研究。
王先生对我们几个学生的出站报告和学位论文都十分上心。刘家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回忆:王先生融通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对地方发展号脉准,找问题和开药方总能独辟蹊径,提出的方案总能让人眼睛一亮。现任西北大学教授的杨新军回忆:王先生在研究和分析地方旅游发展时,非常注重实地调查和对当地传统文化的挖掘与活化。在运城鹳雀楼景区旅游发展策划和运城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实地调研中,每到一个县域或者景区,王先生总是能够敏锐的觉察到该地方或者景区的文化资源基础和旅游发展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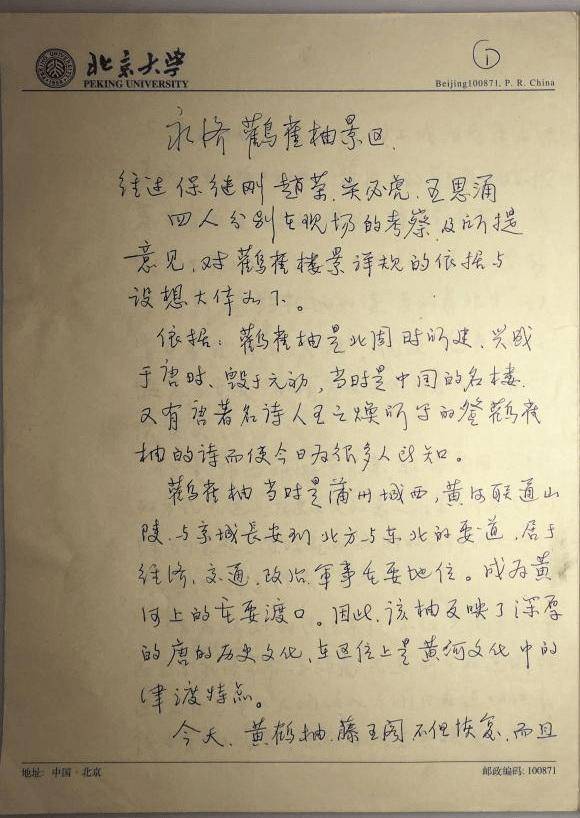
曾在北大陈传康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学位的吴承照(现任同济大学教授)回忆,1989年8月吴承照硕士论文《区域旅游开发理论与实践—以皖南为例》答辩,王先生是答辩主席,在答辩会上王先生肯定了他对新安文化体系的梳理,同时提出今天旅游界最核心的热点话题——文旅融合,王先生说新安文化历史上如此辉煌,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杰出典范,保护与发展应该统筹,新安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是一个大问题,黄山风景与新安文化需要交相辉映,直接关系到徽州与大黄山市发展。从这一点来看,王恩涌先生就是提出文旅融合思想的首倡者也不为过。
曾在北大城环学院就读硕士研究生的吴建峰(现任复旦大学教授)2001年夏季参加了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组织的《安徽省旅游旅游总体规划》编制的工作,考察途中王先生给课题组和安徽省发改委的几位陪同领导上了一堂如何保护自然资源的课程,那次王先生对人地关系的讨论,不仅贯穿在后来的安徽规划中,至今仍影响着吴建峰对城市和区域的理解。
王恩涌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赵荣(毕业后曾任陕西省文物局局长)撰文提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赵荣毕业分配至西北大学任教时,特地将其招至居所,分析其今后教学科研方向,王先生跟赵荣谈到,他有一个未来中国旅游地理研究的设想,希望广东的保继刚(中山大学)从自然地理角度深化旅游资源与规划研究,上海的吴必虎(时在华东师大)从旅游空间过程开拓旅游地理学的重要地位,希望赵荣(时在西北大学)利用西安古都的区位优势,从历史文化资源角度开展旅游研究。他认为,只要我们努力,中国的旅游研究一定会有地理学人的重要地位,旅游地理学甚至是引领旅游事业发展的支撑学科。从中国旅游地理三十年来的发展成果,足以证明王恩涌先生的高瞻远瞩。
王恩涌先生对中国旅游旅游地理学的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对年轻一代学者进入旅游地理和旅游规划研究的深刻影响。据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戴光全博士回忆,2004年6月,戴光全的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王先生还专门跟他通了一个电话,原来他的博士论文王先生是外审专家之一,除了书面给予专业和到位的指导,王先生在电话里跟他探讨了昆明世博会的影响,由于我们的国情和发展阶段跟国外不同,因此二者举办的重大事件其影响应该有很多区别,这是值得进一步注意的问题。当时论文确实没有注意到这个,只是把国外的有关理论拿过来,再用到昆明世博会的研究之中。这件事给了戴光全很深的感受和很大启发。这个电话不仅显示先生具有深厚的学养和研究功力,而且还表达出对后学细致而深深的关爱,第三是作为一个学者“守规矩”的严谨做事态度(在答辩后、修改提交正式稿之前在书面匿名提出评审意见之后再次跟答辩人通电话深入指导)。
以地理学家的专业训练指导区域旅游发展规划研究,现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汪芳博士(本科建筑学出身)提到,三峡规划考察时,王先生带着大家读地图,教课题组怎么把一张平面的地图看出山形水系的立体空间,怎么从地图上看出一个城镇的发展脉络和生长逻辑。考察途中还给年轻人出题,翻开手里的地图册,随意指着一张城市地图便问“能看出来哪里是老城区吗?”,还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解释“张飞庙为什么设在那个湍急转弯的地方?”。对于野外考察的杰出能力这一点在经济学出身的周尚意(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看来,王先生留给她深刻印象的同样也充满传奇色彩。周尚意教授回忆道:“记得大约在2003年,我和王先生等一起会议后的考察。他得知我也喜欢跑野外,就跟我做了一个观察游戏:判断汽车经过聚落的行政等级。游戏后,我跟随车的当地人印证,王先生的判断都是对的。王先生说:野外感觉很重要。这句话对我触动很深,后来我就开始留意训练自己的野外观察能力。” 学以致用,融会贯通,处处是生动的课堂,这就是大先生。
作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一年考取清华然后于1952年随地理系整建制搬家到北大的地质地理系的学生,也就是新中国甫成立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地理学家,王恩涌先生以其独特的地理学视角,产生的学术影响不仅涉及旅游地理和旅业发展,同时也延伸至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王恩涌先生与厉以宁教授在南京读中学时是校友,并与厉以宁先生领导的光华管理学院合作,关注我国的环境生态问题。他曾对厉以宁教授讲经济学是看不见的手,而地理学就是看不见的脚。这一地理学思想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改革开放后初期北大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
以地理学家的广博深邃影响到中国旅游发展的一个具体案例就是曾任国家旅游局多个司局的司长魏小安先生与王先生的君子之交和深厚情谊。魏小安在其专门撰写追怀王恩涌先生的文章中说,拜读了王先生的一系列文章之后“大吃一惊”,王先生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角度,即人文地理学的角度;运用了一套分析手段,综合分析的手段,从中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思想的穿透力”,受到王先生文章的触动,小安还特地花了不少心血帮王先生的文章整理成册,他认为编的这本书中的许多观点和方法都是很有意思的,也都是很有意义的,值得旅业的人士研读,举一反三,必有所悟,必有所获。后来这本书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即《王恩涌文化地理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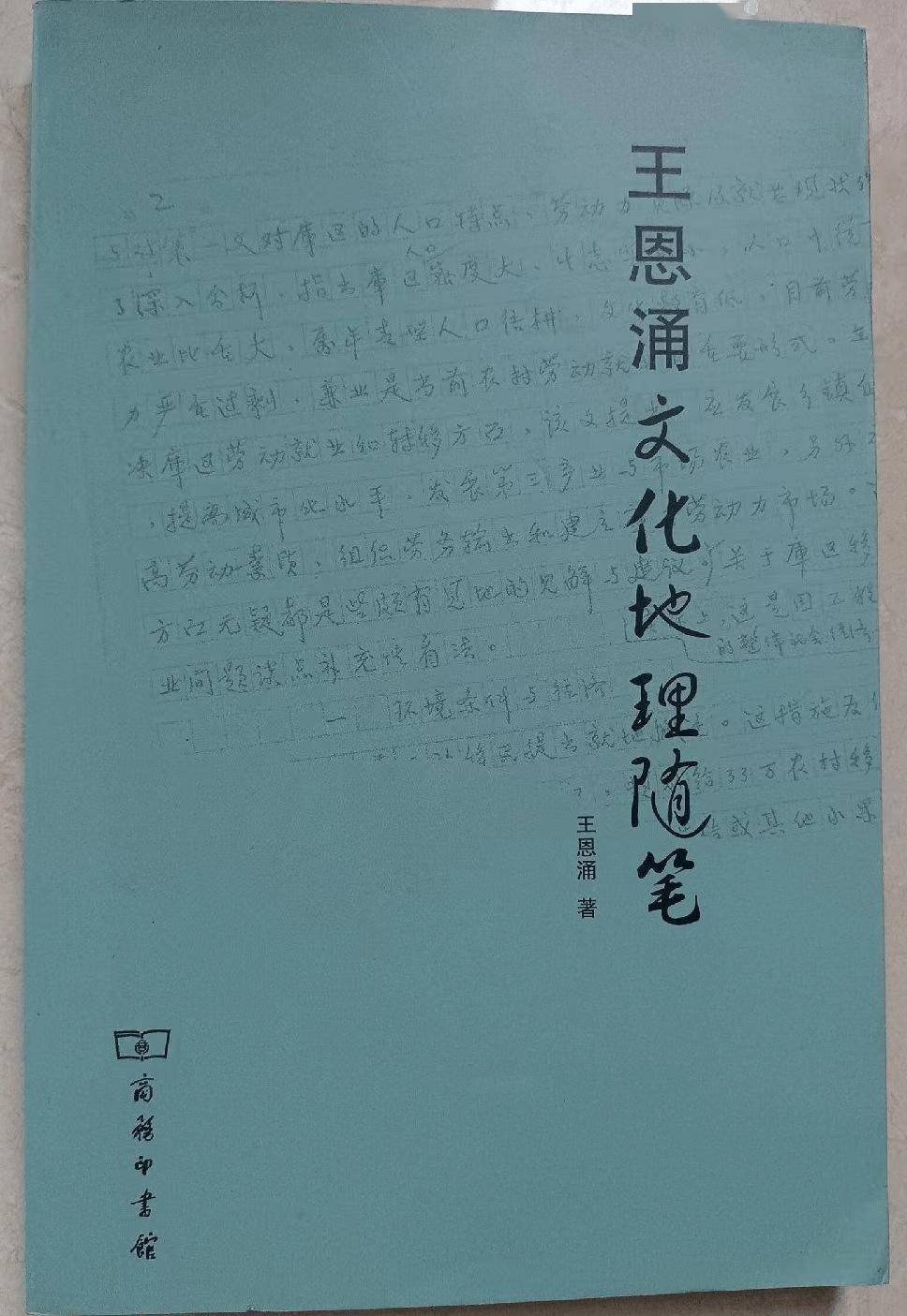
王恩涌先生由早年的植物地理、环境科学等自然地理研究,转而深入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研究,可以称为是现代世界少有的具有综合地理学思想和能力的杰出学者。“将地理环境、社会发展、经济增长、文化遗产、历史进程融为一炉,是王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也是他特有的学术能力。这极大地启示了我们的旅游规划工作”,这是蔡运龙教授在其回忆中特地提及的。区域旅游发展如何植根于当地的历史文化,将文化和旅游融为一体编制发展规划,王恩涌先生很早之前就已提出这样的研究路径,可以称为是中国文旅融合最早的提倡者之一。
长期从事考古、大遗址和文物保护研究及管理工作的赵荣博士回忆,在王恩涌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他将旅游活动引入文物保护规划,创新文物保护与旅游活动、区域发展的关系,主持完成了秦始皇帝陵、周原、安阳殷墟、汉长安城、唐昭陵等保护利用规划。后来主持陕西省文物局工作,推动西安城墙景区活化、大遗址国家公园建设、策划唐华清宫《长恨歌》演出……二十多年来,这些工作无不凝结着王先生深刻的文旅融合学术思想教育和不断的鼓励、提点与指导。
王恩涌先生文旅融合、将历史记载转化为现代旅游吸引物的能力最具体的案例就是内蒙古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文化旅游景区规划的神来之笔。成吉思汗陵原来的面积较小,仅限于祭祀大殿周边。当时我是成陵文旅项目的组长,提出要把范围扩大,做成一个旅游区,用宽阔威严的陵道连接大殿和新区。王先生应邀担任顾问,深度参与规划设计,他从我俩共用的办公室书架上抽出一本很多年前出版的美国《National Geographic》,里面有几幅插图,隐约记得是古代中亚色目人绘制的蒙古征服绘画,其中一幅铁马金帐的画面,以及成吉思汗家族征服的欧亚大陆版图。王先生建议建设铁马金帐群雕、欧亚地图广场等创意。这些创意得到了当地政府的一致同意。景区建成后获得内蒙古第一个5A级旅游景区,并受到多位国家领导人参观访问和认可。


1999年我们承担了辽宁五女山景区规划的任务,王先生再次作为顾问参加了规划研究,在考察五女山的过程中,王先生对山顶地形、遗址布局、城墙构造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当即指出,五女山山城是一座卫城,它和雅典卫城一样,具备了卫城的六个要素:城墙、神庙、宫殿、粮仓、兵营、水源,并提出了“东方第一卫城”的文化定位。这一定位后被桓仁县文化、旅游部门采纳,成为五女山旅游开发中一张闪亮的名片,随着2004年五女山山城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生为五女山打造的这张名片更加光彩夺目。五女山研究再一次显示了王先生文旅融合的深刻意义。
王恩涌先生学术一生,大学毕业之后的前三十年主要贡献给了行政事务并伴随着无法回避的政治运动,后四十年则投身于迟到的学术生涯。由早期的自然地理训练转向人文地理开创,尤其在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方面独辟蹊径,影响超出地理学之外。王先生的学术魅力和研究成果,正式见之于所谓核心期刊的并不多,而更多地表现在其“思想的穿透力”以及在此穿透力支撑下的学术专著和教材编写。他的另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是科研组织和学科领导力。他的思想穿透力和学科领导力,体现在旅游研究方面,不仅为北大的旅游研究和旅游规划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也以一个伟大地理学家的深刻见解和灵活运用,积极影响了中国旅游学术和旅游产业的发展。